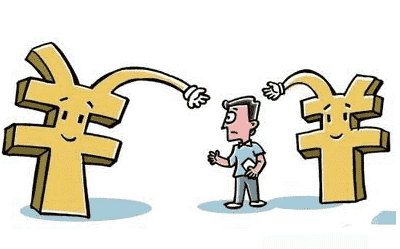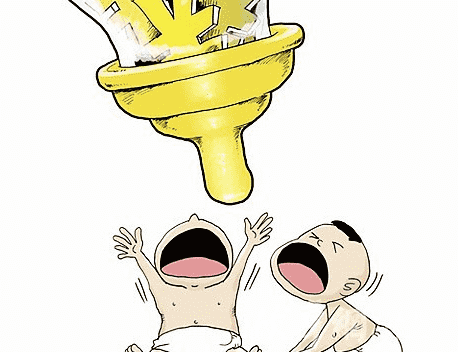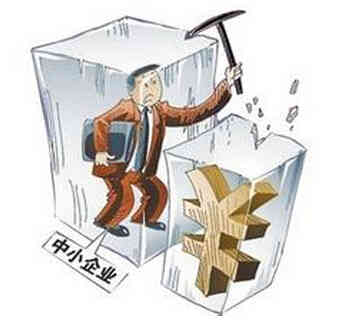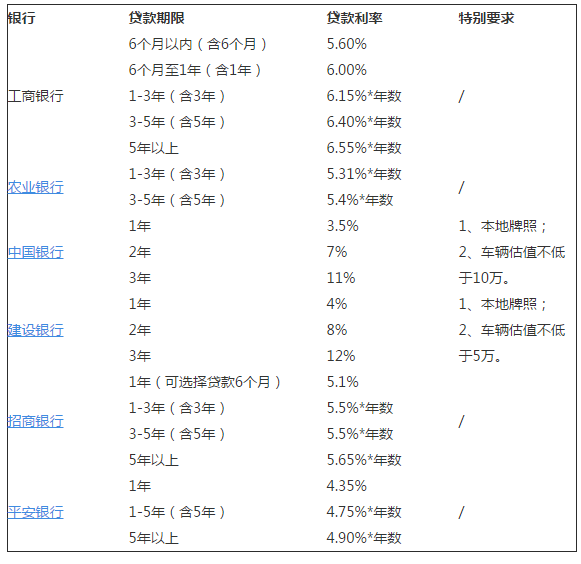国有银行的贷款策略容易造就坏企业
原标题:国有银行的贷款策略容易造就坏企业
放松管制和开放民营是银行重建信誉机制的出路
赵晓:你对金融管制怎么看?
张维迎:金融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一是金融行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为严重,从债务人做出承诺到兑现这种承诺的时间也更长,这样的话,机会主义、欺骗行为可能会产生。另一方面,金融业有较强的外部性,涉及到整个货币体系,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金融业的这些特性使得人们通常认为有必要对金融业加以管制。
但就现在来讲,我想我们国家对金融业的管制远远多于它应该管的。因此,金融业更多的应该是允许和提倡竞争。我们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标杆,比如说资产必须在多少以上才可以开银行。但是,只要达到这个标杆就一定不能有歧视,不可以批张三不批李四。谁先符合这个条件,谁先进入。
并非对金融业的管制越多,欺诈行为就越少。现在我们的管制很多,但坏帐更多。看看当年山西票号的情况,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100多年的历史中,它并没有什么欺诈行为啊!那时候,办银行不需要审批,没有中央银行,也谈不上什么监管,也没有计算机传递信息。它靠什么呢?靠的是信誉。
但是,管制太多,信誉就没有了。在政府管制下,已经进入的银行拥有垄断权,可以坐享丰厚的垄断利润,干嘛还要建立信誉?在利率自由化的情况下,信誉好的银行可以给存款人付低的利息,不好的银行则要付高的利息,因此银行都有积极性建立良好的信誉。但是如果实行利率管制,我信誉再好,我和别人支付的利率是一样的,那我何必建立信誉?
在中国还有个产权问题,也就是说,因为金融机构是国家的,就更不会有信誉机制了。既然是国家的银行,老百姓知道反正有政府兜着,把钱存在那一个银行都是一样,他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择银行,或者去惩罚信誉不好的银行。
金融管制已经影响了中国的银行提高效率、建立信誉,所以金融业迟早要开放竞争。我再重复一下,可以设一个进入标杆,但只要达到这个标杆,任何人都可以办银行。
赵晓:现在发展民营银行的呼声已经起来了,但是国有银行的人认为没有操作性。
张维迎:任何法定垄断领域,如果有人想进入,垄断者一定会游说政府,找出无数的垄断好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本能的反应。垄断者很清楚,就谋取最大利益来说,没有什么比法定垄断更好的手段,至少他可以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过一个清闲的生活”。所以,我想国有银行的反对是很自然的。
但实际上未来更应该搞的是民营银行。国有银行由政府兜着,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提高效率,效率不高怎么和外资银行竞争?所以未来一定是民营银行的天下。只有民营银行才会有积极性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如果说国家一定要办银行,办商业银行还马马虎虎,投资银行绝对不能去搞。投资银行要求非常灵活的体制,非常强的激励机制,这些政府根本办不到,政府搞投资银行肯定失败。
投资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信用的需求。以投资银行为例,为什么卖股票的企业不直接去市场摆摊,而是要通过投资银行来间接地卖呢?因为前一种情况投资者更容易受欺骗,企业也就更不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所以投资者不愿意出高的价格。而投资银行以自己的信誉担保企业的价值,投资者就愿意出高价。但如果这些机构本身不讲信用,它存在的意义就都没了。
在国外,投资银行一定要靠说真话、靠信誉来赚钱。国内的证券公司现在基本是通过说假话来赚钱。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为什么说假话还能赚钱?当然是因为垄断地位和政府管制。所以,放松管制和发展民营银行是国内银行建立信誉机制的出路所在。
赵晓:民营银行是早点还是晚点放开好呢?
张维迎:也许应该这么来想,如果我们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有计划地放开私人银行,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产生一些非常大、非常强的私人银行了,但我们没有。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放开,那么五年、十年后放开,中国的金融业一定会更加被动。当然,外国银行的进入会带来好的信誉,对维持市场的稳定也有好处,但中国的老百姓在感情上可能不容易接受。
民营银行的发展有一定风险,但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现在发展民营银行,不会从一个人先卖土豆赚了钱再开始。中国已经有大量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股份制银行也起步了。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从股份制银行开始?另外,国有银行也可以搞民营化的试点。
赵晓:难道国有银行就一定贷不好款?
张维迎:国有银行贷不好款事出有因。当市场上企业的信誉建立起来时,你愿意把钱贷给谁?肯定愿意找一个好的企业。但现在好的企业特别少,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找好的企业?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如果这个企业是政府圈定的重点企业,企业老总评过全国优秀,所有的银行都有积极性去找它。这个企业的钱就会花不完。当自由现金(freecash-flow)多的时候,管理人员就开始胡闹。这样,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企业,由于银行拼命给它授信、给它放贷,最后变成了一个坏企业。
国有银行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譬如,贷款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给民营企业。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一旦垮了,贷款还不上,别人可能怀疑你吃了回扣,而国有银行贷给好的国有企业,尽管到时候它也可能出事,但贷的时候它毕竟是好的啊,大家都是同意给他贷的,贷款人的责任轻多了。
因此,贷款人的机会主义,谁也不愿承担贷款责任和风险的做法,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集体性地创造一批坏企业出来。除非通过产权变革,使得银行能够自身去承担责任,否则贷不好款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想,如果国家在放松银行管制上有比较大的动作的话,可以给社会一个信号,证明政府有一个承诺,会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化,从而产生一个额外的“信誉”收益。
政府的垄断和管制大量创造“股市骗子”
赵晓:中国证券市场政府管制最多,任何一个企业上市都必须得到政府好几个部门的审批,但问题也最多。最近“基金黑幕”、“庄家操纵股市”的报道一个接一个。你对证券业的管制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与管制有关,同时也与产权有关。在中国这个市场,缺少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政府对股票市场随意地管制和利用,大家对股市没有稳定的预期,不出这样的问题才怪呢!
我们知道一句话,“自己掐不死自己”。好比现在大人跟孩子讲:“你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大人的话小孩是不会信的,因为这话本身就是不可信的。同样,如果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是政府的企业,政府是很难下手的。这跟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要是名声坏了,声誉坏了,它也就完蛋了。但如果这是国有企业,市场要你死,政府还想让你活呢。这样一种行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必然对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出现了很多的骗子,那么一定会有受害者。受害者不一定有办法用法律手段起诉欺骗他的人,但他还是有一招,就是不再买你的股票,不再跟你作交易。这是他对你最后的惩罚。你因为担心这一点,行为就会变得老实一些,规范一些,就会讲信誉。现在我们的市场,有那么多骗子,相应有更多的受害者。那些受害人,比如说散户,没有多大的力量,但他们可以选择“退出”,对市场上的骗子进行惩罚,结果可能就是市场交易的急剧萎缩。
但是,中国这个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年,它并没有出现交易的急剧萎缩,相反,股民们还是奋不顾身地往里冲。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如果政府承担了培育市场、扩展市场的责任,那么这个股票市场现在是不能萎缩的,它必须不断地发展,而政府可以想方设法使得受骗的人也不退出这个市场。政府如何能让受骗的人也不退出这个市场呢?一个办法就是给受骗的人进行补偿。由于政府给了受骗人补偿,所以受骗人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受到损害,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继续在市场交易。当然,这样一来,那些骗子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继续行骗。我们目前的体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体制。
我一直在想,中国这么一个股市,明明上市公司没有收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小股民一个劲地往里冲?他一定是有好的预期啊!他一定觉得他可能得到的好处比他可能受到的欺骗加上其他成本要大,他才愿意往上冲。因为这个股市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持续了十来年啊!最后我发现事情可能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股市,所有冲进股市的人,除非你运气特别不好,否则都会得到一些好处。
那么,骗子们拿走的钱是谁支付的呢?是那些在股市外的人支付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琼民源,作假账垮了,买他股票的人受骗上当。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股民就会受损,就会学乖,他以后会更加小心地去了解一个企业,慎重买股票。但是我们采取什么办法?琼民源垮了,股民有意见,说这个市场不规范,他们要闹事,政府就把中关村科技这个名称给了琼民源,而琼民源原来濒临破产的股东,受骗的股东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关村科技的股东,股价翻番,皆大欢喜。你想想,中关村科技包含了多少因为政府管制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
如果这样一而再而三的话,大家就会形成稳定的预期:没关系,我知道股市有骗子,我可能会被骗,但如果我真的受骗了,政府会从其他的渠道来补偿我的,如果将来“中关村科技”也不行了,换成其他什么科技就是了,所以我受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应该冲进去。这样就使得股票市场泡沫、黑幕、骗子越来越多。
赵晓:为什么过去场外人中没有谁想到这一点,也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头?
张维迎:经济学证明,集体行动存在着许多悖论。我们可以联想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英国,国王大量地借私人贷款,但又任意地、随时地修改贷款的合同,延期还款、降低利息等等。如果债权人预期到国王这样做,就不会给他借款,或者可以联合采取对策。但问题在于,这些人很多,国王总是可以贿赂其中的一部分人,让反对给他借款的联盟不能形成。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好多破产法规定都要有一个“优先程序(priority)”,还要有“债权人会议”,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行动的“囚徒困境”问题。否则,我这个企业要破产,我欠100个人的债,其中也欠你的,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债权人,他们的钱我都不还,我只还你的,把你安抚住,你还继续给我支持,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建立信誉了。
股票市场的情况与此类似。政府用场外人应该享有的资源补场内,是因为股民很集中,有这个要求,而场外的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很分散,而且利益相对间接,尽管大家有利益在里边,但不可能形成合力阻止政府这样做。而且,个人明智的选择,与其发出声音阻止政府这样做,还不如自己直接进场寻租更好。所以我说中国股市上一个“寻租场”。
这跟当年的农村城市关系有点类似。城市人离政府近,说话的声音高,农民尽管人数众多,但离政府远,说话的声音低而分散。所以政府就用剪刀差来剥削农民。
赵晓:愚公移山信心十足,因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现在中国的股市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原来是因为“国有资产无穷尽也”?
张维迎:资源当然不会无穷无尽,但现在还没有耗尽。你犯了错误,政府必然会调用其他的资源来掩盖你的错误,政府的隐含担保使得所有在股市上玩的人,所有进场的人都预期不会受到损害。
我还想说说郑百文的事例。在西方,如果说企业垮了,股票将一钱不值,但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可能创造出对壳的需求。比如,山东的三联有积极性去买这个壳。这个壳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管制租金。这个壳又可以使得那些受骗的股民得到补偿,ST郑百文的股价还可以涨停板。
在市场中,破产的企业是不可能有人来买的,不会再有你的牌子了;即使买,也不付多少钱。我要上市,我自己可以上市,我干吗披着你的外衣?但中国不同,上市是政府的垄断行为,我自己上不了市,就只能借壳上市。
你去卖西红柿的时候,如果烂的西红柿和好的西红柿搁一块的话,好的西红柿的价钱也会掉下来。但我们的问题是,好的西红柿不让卖,只能卖烂的西红柿,所以我为了卖我的好西红柿,只好将它塞进你的烂西红柿中混着卖。当前股市上烂的西红柿很值钱,损害的是好的西红柿应有的价格。
赵晓:你说损害了好西红柿的价格。在郑百文的案例中,山东三联是不是这个好西红柿?如果买壳对三联的利益有损,那为什么三联还要买呢?
张维迎:受损的是全中国所有的好西红柿整体。买壳对三联是有好处的,我说过所有入场的人都能预期得到些好处。我是个大投机商,我做庄,我骗了你一把,我赚大钱。你是个小股民,你损失了100。但是,你不要害怕,政府会补给你120,你满意了吧?原来股市上的120是政府垄断转移来的。
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确实类似一个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因为垄断有效率损失),但对场内的人而言,是一个正和博弈,是用120的场外资源来维持场内皆大欢喜的局面。可见,中国股市确实存在着场内人与场外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没有外部输血,没有政府资源的进入,如果受骗者得不到补偿,这个股市就没法继续持续下去。
赵晓:那么,这个游戏能永远持续吗?
张维迎:不能。好比说有10个人,政府对每个人收100万块钱,许诺给10套房,政府收到1000万块钱。但政府花钱的效率很差,1000万只建了4套房子,只有4个人能够得到,所以大家都去抢这个房子去,抢到房子的人很高兴,没抢到房子的人就觉得吃亏了,要闹事。政府怎么安慰呢?再向另外的1000人征税,给要闹事的人再买几套房子。然后是再收钱,再建房,但总是建不够应有的房子,这样又会有人不满意,再闹,再输血。一直闹到最后,没有新的资源,不能再输血了,这个博弈也就完了。
所以,中国的股市是个资金黑洞,什么时候国家把能够运用的资源用完了也就完了。从时间看,也许不需要到这个时候,一旦发出一个崩盘的信号,或者大家预期到场外资源要用完,股市就会崩盘。然后,股票市场再慢慢走上正轨。
赵晓:这让我想起来杂耍中的“锅盖舞”,三个盖盖五个锅,你看任何一个锅都有盖,但要是同时检查五个锅,就会露馅了。
张维迎:能玩到这个地步,那是高手。我担心玩不到这个地步。股市中的欺骗其实是政府有意无意地造成的。政府为了防止欺骗,他又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好比说规定上市公司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才能增发配股,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进一步的短期行为。试想,我上市后募集了1个亿的资金,加上我原来1个亿,我每年必须有2000万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盈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怎么办呢?它自己就最有积极性去做庄炒作。
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在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可能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怎么能够第一年就拿出10%的回报呢?从理论上,这个东西并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
赵晓:将“信贷配给理论”运用于证券市场,这非常有意思。
张维迎: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可见,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的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骗子进来。
赵晓:在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中,存在着人为的户籍制度,农民的身份很难转换。但股市不是这样,谁都可以进。既然国家保证股市赢利,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炒股?
张维迎:这是因为每个人进股市的成本相差很大。比如说好多人住在偏远的地方,还比如说有的人太忙,或者缺乏兴趣。
不过,起作用的机制是一样。户籍制度无非是使得你进城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但即使在户籍制度最严格的时候,想进城也不是不可能。比如你可以买通官员,弄个城市户口,当然那样做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更多的是有门路的人,从农民变成了城市人。但股市不是这样,它其实是一部分边缘的人、机会成本比较低的人进入了股市,机会成本比较高的人则不进入股市。
赵晓:2000年政府支持力度大,股市盈利好,股指上升快,新开户数据说增加了三成。应该说这与你的分析是一致的。
张维迎:这是肯定的。政府在拉市的时候,投资者预期到政府转移的资源增加,于是进入的也就越多。如果政府打压股市,那当然不会有人跟进。
赵晓:地方政府是否与之有关?
张维迎:前面主要从宏观上讲中央政府与股民及社会的博弈。从微观上讲,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积极性去维持这个虚假的股市。好比说,这个企业是我地方的企业,是我批准、我走关系才取得上市资格的,因此企业上市等于说地方政府起了保荐人的作用,怎么维护这个企业上市地位对地方政府就很重要。如果仅仅是一个企业,完蛋了就完蛋了。但企业后边的老板是政府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利用地方的资源给他注资,好让它维持下去。什么时候注资呢?在股票标成“ST”的时候!
所以,权力越大,监督越难,腐败越多。你甚至还可以用难于监督的那部分权力去掩盖容易监督的那部分权力。在证券市场,如果某个企业亏损了,那么我还可以用其他的企业来弥补它;如果一批人被套了,我还可以想办法用场外的资源来为他们解套。